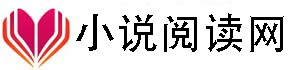30-40(15/31)
子叫我闭嘴吗?我远走高飞,在世界的尽头失去了宣扬幸福的能力,但我的爱人可以,他把我散架的骨头一块一块拼起来,让我发声。父亲,就算如此,想必您也对狡诈很有信心吧,因为您知道破镜没法重圆,伤口永远都会留下疤痕。您摧毁了我对爱的一切认知,却十分人性化地留了一条缝,让我透过这条缝窥探爱。您知道哪怕我突破这条缝,往外生根发芽,开出的花也是畸形的。
父亲,您最好的杰作是我,不是您的两个儿子,您塑造了一个渴望快乐同时偏爱痛苦的怪物,一个满世界
寻找有名的画作然后亲手把它烧毁的怪物。
父亲,我失去了丰富的表情,您不允许我缩回蛋壳里,但我必须缩回蛋壳里,找回掉落的第一颗乳牙。这是暴虐之罪,乳牙掉落是暴虐之罪。
父亲,而您犯了欺瞒之罪。我尊敬您,因为尊敬您,我才能全心全意地恨您。您欺瞒我,对我说,幸福是痛苦的开始,是痛苦的最高级别,乃至一份微笑都被您奚落地遍体鳞伤。一百分是退步的开始,夸奖是自负的开始,交友是孤立的开始,仰慕是强。奸的开始。我从小与您对抗,却在潜意识里听信了您的馋言。我恨您,到生命结束为止,我都将如此恨下去。
我终究还是怀着“到底什么是个头啊”的想法睡过去,醒来时想起了一路上的沉默寡言,伊实一定吓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眼里有光的小孩在接到捧花那一刻变得惊慌失措,变得只有苦笑和反叛似的一言不发。只因为我说了一句:我突然累了,请让我休息一会儿。他便安排妥当所有行程,掀开被褥,将我拥入怀中,轻拍我的后背,讲天南海北的故事。
“穆里斯,这不是摆布,这是幸福。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我完全没有对策了,只想着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心甘情愿对你百依百顺,只要你是我的。
“我开始认识到我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了,不是指折腾来折腾去,而是……离奇地想要你融入我生活里的每一秒。
“穆里斯,只要你想,怎么对我都行。”
我都听见了,伊实,你的爱足够响亮,我都能听见,但你忘了,你我的初见是在一个时日不多的暴风雪夜,延续生命同斩断生命一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今日的礼炮对我猛烈撞击,撞击我歪歪斜斜地向前扑倒。在引文里就写上大结局的故事,不得善终。
……
回到罗弗敦的家,是的,我称之为家,和伊实待久了,越来越喜欢不计后果地对曾经质疑的东西赋予一个交代。回到罗弗敦的家,我寻找我的行李箱,它曾在客厅流浪了一阵子,后来有了固定住所,但我不知道在哪儿。
伊实从仓库里把我的行李箱推出来的时候我决定生个不影响局势但需要哄的气。
“Why?我认为你再也用不到它了。”伊实说得天经地义。
“再把它乱丢我会让你好看。”我骂道,凶巴巴地放倒行李箱。
里面其实没什么好东西,只有一些证件,没电的手机,和几张百元人民币,在这里都用不上。晕,原来洗护用品一样没装进去,知道的倒是不在乎什么自杀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来当北欧当野人。
“伊实。”我喊道,背后没应声,我提高音量又喊了一遍:“伊实!”
“我在!”脚步声从厨房由远及近。
我举着手机问:“你有适合的充电器吗?”
伊实惊讶于我竟然拥有属于自己的通讯工具,大有装疯卖傻的嫌疑:“我还以为你们中国人交流都靠写信,withpigeonorsomething。”
我把手机交给他,说:“嗯,以后你要和我说什么话请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