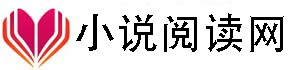20-30(2/34)
池倾心头不知瞬息闪过什么,收回手,捏着他的下巴用力地吻上。本就相贴的肌肤因此越发亲密无间,池倾身上的花香无孔不入,扑满谢衡玉的鼻端,他细细看着她闭眼的样子,与之深深相拥。
清湖州的春天比戈壁州来得早,这又是个提前的暖春。
去年秋季扎根深土的根须,也会于纠缠间沉进温暖湿软的土壤,在一场惊蛰的大雨之后迸发出崭新的生命。
不知多久过去,飞马自九天之上下落。最终落定时,依旧停于云上,它收起翅膀站定,半晌有些焦躁地嘶鸣了一声。
车厢内衣衫凌乱,环佩散落,池倾尚有些迷糊地躺在谢衡玉怀中,任凭他动作轻柔地替她拭净水渍,穿上衣袍,重新用发带系住她散乱的长发。
待她诸事稳妥,谢衡玉才转身拾起地上的衣衫,一件件抚平穿上。他上身半裸,劲瘦宽阔的肩背上纵横着她留下的痕迹,微红的,有些凌乱,在那痕迹之下,却是陈年的刀伤和……杖痕。
车厢内光线昏暗,但池倾还是看清了那些令人心惊的印记。心底突然生出无名的怒火,她伸手抚上那纵横的伤疤,指尖沿着那不断的痕迹划过,呼吸轻滞,涩声道:“这是什么?为何会留疤?”
谢衡玉的身体在她指尖落上腰背的瞬间便已微僵,他披上里衣,握住她的手转过身来,半跪在她身前,侧脸贴了贴她的手背:“都过去了。”
池倾却不依不饶:“这是家法?”
谢衡玉垂眸,平静道:“差不多。”
与谢衡玉的成长相伴的,除了谢衡瑾如影随形的阴影,再便是谢家主母日复一日崩溃的精神。
随着谢衡玉一点点长大,在人前越发出色,无可挑剔。作为母亲,唐梨却越发无法将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
谢衡瑾去世的时候还很小,唐梨并未见过孩子长大后的模样。
若说十岁的谢衡玉尚还有未脱的稚气,会令唐梨时常恍惚他与幼子的差别,但当他快速摆脱那种稚嫩的气质,蜕变为眉目俊朗的少年时,唐梨的自欺欺人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谢衡玉在人前越是风光无限,越是美名远扬,落在她耳朵里,便越发如同行盗玉窃钩之事的可恨小贼——占了她留给亲子的资源,还抢了那个可怜孩子的人生。
虽说有些时候,唐梨是会清醒的。但那短暂的忏悔和怜悯,并没能敌过她对早夭幼子的愧疚和思念。
她心中像是居着魔,迷着障,只有看到谢衡玉跪在她面前,被打到血肉模糊之时,才能稍稍缓解几分心中的痛意。
她身子不好,手边唯一可以杖责他的,便是那把轻巧的本命剑——那是件法器,随主人的心意而变,虽然轻盈,留下的伤痕难以治愈。
谢家家主谢渭心疼夫人,因此不常会阻拦唐梨的发泄,只有打得实在过火时,才会勉强将谢衡玉带出来。
后来,等谢衡玉再大一点,体质筋骨更加强劲了,谢渭便更加不用出手,索性不闻不问。反正即便夫人打到失了力,谢衡玉依旧能自己走出来。
世俗礼法、父母之恩、救济之宜,是一座座越不过去的大山。彼时人人都在可怜唐梨,面对谢衡玉,也只是劝慰他别多想。
再多心一点,便要论对错,而牵扯了情分的对错,向来论不清长短。
事实上,没人觉得唐梨有错,也没人觉得谢渭有错,而谢衡玉……他更没有错,只是命该如此。
得到了取之不尽的顶尖资源,取得了万人仰望的地位名望,也总该为此付出代价。
赤日尚有阴云遮蔽之时,何况生而为人呢?
大家都